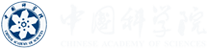|
基金会动态
|
传媒扫描
一九七八年三月,一个和煦的春夜里,刚参加过五届人大回到昆明的云南植物研究所所长、著名植物学家吴征镒,对来访的记者说:“参加了五届人大,我最突出的感受是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在‘四人邦’横行时,踏踏实实工作的人受迫害。‘四人邦’要的是吹嘘拍马的人,他们搞的是伪科学,实际上是不要科学。什么叫科学?科学就是深入到最复杂事物中去找出其发生发已规律的一种工作,譬如我搞植物学,就要以植物为对象,深入进去,弄清哪些是有用的,哪些是暂时没有用的。现今世界上已发现的植物有三十多万种,我国有二万五千多种。这二万五千种如果有十分之一能用在国民经济上也不得了。要做许许多多的工作啊!”。 “我长期养成的习惯是:工作、工作,一天不工作,比什么都难受。而林彪、‘四人邦’剥夺我工作的权利有四、五年之久。他们说我是‘个人奋斗’、‘成名成家’。其实我想的只是我国有这么多的植物,要尽可能地认识它、掌握它,让它为人民造福!” 话虽简单,但却是对林彪、“四人邦”扼杀我国科学事业,摧残我国科学队伍滔天罪行的忿怒控诉!今天,“四人邦”已经垮台了,被他们颠倒的历史必须纠正,被他们搅乱的是非必须澄清,老实人应当受到赞扬,有贡献的人应当受到尊敬,正气必然伸张于天地之间! 一 一九三七年,吴征镒在清华大学毕业了,当时他读到一本名叫《中国的西北角》的书,引起了他对祖国大西北的向往。于是就抱着科学救国的思想,参加了一个科学考察团,到了内蒙古一带,研究在那里移民开荒的可能性。“七七”事变爆发了。考察团抵达宁夏的那一天,传来了北平沦陷的消息。这一次考察也就半途夭折了。在旅途中,他们穿越了一个又一个雕敝破败的村庄,也看到了黄河船夫的悲惨痛苦的生活。这一切使他开始感到这个古老国家是到了生死存亡之秋了!书斋是呆不住了,但是出路何在呢? 不久,学校撤退到了长沙,侵略者的炸弹也跟踪而来,湘庭湖之南也摆不下一张书桌了。一九三七年十一月,由清华、北大、南开组成的长沙临时大学决定向大西南撤退。二百多名学生,十三名教师,包括已成为生物系助教的吴征镒,和以后拍案而起的闻一多先生,花了三个多月时间,步行三千多里,到达昆明。这次旅行给他上了一堂前所未有、内容极其深广的社会学课程。大后方的帷幕一层一层地在他眼前揭开;一边是灯红酒绿,后庭花开;一边是妻离子散,积尸郊野。国民党反动政治的极端腐败,人民在水深火热中,使他对中了的现实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但是,真正使他彻底抛弃“科学救国”幻想的是这样一件事:一九四四年,他最敬爱的老师、清华大学生物系教授吴蕴珍,在饱经了生活的折磨后,于贫疾交迫中死去了。这是一个有真才实学的植物分类学家。他对发展我国的植物科学,怀有很大的抱负,但还没有来得及拿出什么成就,就被旧社会吞噬了!吴征镒非常悲痛,他写下了哀悼老师的诗:“图形翻本草,名物记拉丁;贫疾劳知已,凄凉付阁棺”。老师的工作留给了他,但他从老师的遭遇想到自己渺茫的前途。“这条路走不得了!”他终于下了决心。为寄托自己的感情,他写了一首题为《求真者》的诗。诗中描写一个独自在沙漠里,像寻找泉水一样寻找真理的人,他有许多美丽的幻想,遇到过许多恶毒的嘲弄,看到了虚无缥缈的海市蜃楼,最后终于倒下去了。但就在这时候,他看到了“斗大的朝阳从东方升起”,于是他又苏醒过来,鼓起勇气和信心,继续走下去寻找真理。 那个太阳升起的地方,他指的是延安。这个寻求真理的人就是他自己。 吴征镒拒绝了被推荐留学美国哈佛大学生物系的强烈诱惑,奋身投入了汹涌的革命浪潮。一九四五年,发生了震惊全国的昆明“一·二一”惨案,他参加了追悼“四烈士”的抬棺游行,在国民党“省党部”的门前设路祭,朗读反蒋的祭文。他经受了李公朴、闻一多被刺的刺激,目睹了周围的一些人高升、退隐和沉沦的变迁。他决心献身革命,一九四六年二月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暗夜风雷迅,前军没大星。”“轻身凭胆赤,赴死见年青。”他写下这些诗句,用以纪念闻一多先生之死,并勉励自己。 一九四八年底,共产党员吴征镒从北中解放区回到了北平,参加接管清华、燕京两年大学的工作。他穿一件灰棉军大衣,每天冒着严寒从青龙桥步行到清华,在教授、研究人员中做思想工作,把党的关怀和温暖带给他们。 中国科学院成立后,他是第一任党支部书记,他住在单身宿舍里,还是像进城初期一样,每天要深夜十二点才回去。他在操劳些什么,许多人不知道,但是他们看到,北京的植物研究所成立了,动物研究所成立了,海洋生物、遗传、微生物等研究所成立了。南京、昆明、庐山、西北等地生物学方面的研究所和工作站也成立了。科学院在迅速成长壮大起来。直到今天,当回忆起科学院的这一段创业史时,那些老一代的科学家们都异口同声说:“这都同老吴分不开啊!” 二 一九五八年,科学院学部委员、北京植物研究所副所长吴征镒,根据自己的要求,全家从北京搬来云南落户了。 云南是著名的植物王国。早在中生代以前,世界还是一块完整的大陆。以后海底扩张,这个完整的大陆分成了两部分——古南大陆和古北大陆。地壳的变动,将地质古北大陆的云南和西藏抬起,成了今天的滇藏高原。照吴征镒看来,世界植物的起源,在北纬二十度至四十度之间,包括了我国南部的大片地区,而其中地处古北大陆之南和古南大陆之北的滇藏高原,则成了现代有花结果植物的摇篮。这里的植物是这样复杂、丰富、弄清这里的植物,就可以现出中国、东亚以至整个北温带植物的来龙去脉。一个最理想的巨大系统的实验室,全国已发现的植物种类中,有一半这里都有。这里是植物学家们所瞩目的地方,有热带、温带、寒带各种气候各种植物都可以在这里引种和进行控制、改造、还在抗战时期,吴征镒就对云南的植物进行了考察研究,走遍了滇南、滇西,到了丽江,上了鸡足山,写出了《滇南本草图谱》,整理和考证了吴其浚的《植物名实图考》和兰茂的《滇南本草》。落户云南前后,他又撰写和主编了《中国植被区划草图》、《中国植物志》、《中国植物图鉴》、《云南植物志》等著作和资料的部分。一九六四年,他在北京科学讨论会上提出了《中国植物区系的热带亲源》的论文,指出中国植物区系与东南亚热带区系有经第三纪古热带区系传下来的成分,我国西南地区可能是东南亚区系的核心,进而从理论上提出了它可能是北美和欧洲植物发源地的设想。他创立了自己的学说。他在中国植物区系和分类方面付出了大量的心血他坚信,把这些工作做好了,就能找到一把打开中国植物资源宝库的钥匙。 为了找到这把钥匙,多年来,他废寝忘食地工作,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他没有星期日,没有节日。他的行李很简单,除了几件换洗衣服,大部是书籍。他有一本须臾不离的笔记本。外出开会,汽车一停,他就下车观察周围的植物,汽车一开,他就在车上作记录。“不知谁催我,三更灯火五更鸡”,他感到有一种力量鞭策他。 这种精神是足以感动上帝的,但是却触怒了林彪“四人邦”。那些紧跟“四人邦”的人把他关进了“牛棚”,给他戴上了各种各样的大帽子,安下了一个又一个罪名,什么“走资派”、“反动权威”、“由专道路”、“脱离实际”、“死钻书本”、“洋奴哲学”、“爬行主义”、“安、钻、迷典型”等等,等等。 关进“牛棚”,他没有怨言。对那些没完没了、永无休止的咒骂、诬蔑和诽谤,他也不在意。但是使他痛心的是被剥夺了工作权利,丧失了工作时间。他想方设法要在这“牛棚”里找一点回来。 每天,他要被监督着下田劳动。本来做标本也是劳动,他要求进标本室,得不到允许,于是,他在下田劳动时,一边干活,一边观察,把看见的东西记在脑子里,回来就追记,写成了一本《黑龙潭附近田间杂草名录》,载明了水田长什么杂草,旱地长什么杂草,它们的生长条件是什么,为田间除草提供了科学依据。在此期间,一个群众性的中草药搜集整理活动正在全国开展。在“牛棚”里他也能偶然得到这一类小册子使他欣喜的是,里面有许多新的东西。他盼望为这个群众性的创举做出贡献,叹到:“我有的经验,是赤脚医生们没有的。要把我知道的东西同他们结合起来。”他开始着手写一本《长江以南中草药名录》。白天要下地,他就抓紧早晚的一点时间。资料室和标本室关闭了,他凭着脑子里记忆的植物名录等资料进行工作。他的住处只有一只方凳和一张床。翻起被窝,这张床就成了他的桌子。他就在这张床上,对他所能见到的中草药资料进行了系统的整理、研究和总结,从分类学的角度上,他对一百二十多种中草药书中的八十多处错误一一进行了订正。这一切都被周围的同志看在眼里,他们是那样热爱他、同情他,有的人指着“同走资派勾结”的罪名和遭到批斗的危险,偷偷给他送来有关的资料。有的“专案”人员也被感动了,主动来为他抄稿子。现在翻开这几本厚厚的名录来看、发黄的劣质纸张,上面用圆珠笔密密麻麻地写下了六、七十万蝇头小楷中文字和拉丁字,使人看到以后不能不深受感动。再仔细看看,名录中的各条记载,引用了从《神农本草》到现代的资料。但引用的资料只有书名,而没有页数。他是全凭记忆力在工作啊! 三 前些年,不知从那里冒出来一种所谓科研工作必须“一竿子到底”的理论,细说这样作就是科研为生产服务,譬如,搞植物研究,就必须拿出粮食。于是,孟德尔定律没有用了,而这恰恰是杂交物种工作中最基本的道理。吴征镒所搞的植物区系等研究,自然也就成了“脱离实际”的东西。在这段期间,搞植物区划工作成了罪行,谁搞谁倒霉。分类工作打了,标本室的工作作人员被赶下去了,六、七十万份标本有一半被搬走了。直到一九七二年,敬爱的周总理关于加强基础理论研究的指示下达后,这些工作才逐步恢复。 植物学是一门古老的学科,文献资料要靠长期积累。吴征镒十分看重标本工作。他常常勉励年青同志们,不要轻视这个,这是奠基石的工作,是为后人铺平道路的工作。他说当年他从长沙步行到昆明,就是边走边采集标本的,一直到现在,这个工作也没有间断过。与此相应的是,他还搞了一套卡片,这是他青年时代从老师吴蕴珍那里继承下来的。整整十年,搞出了四万多张,这已成了我国植物分类学科上一套最基本的重要参考资料。正因为有了这样坚实的基础,他的知识才有今天这样渊博。这是“脱离实际”吗?当然不是。吴征镒是站在学科发展的高度上,从掌握规律入手,探索自然界的奥秘,为国家寻找最需要的植物资源。他的行动,给研究所带来了一种不图虚名、不赶时髦的踏踏实实的作风。他的指导思想,使研究工作避免了盲目和混乱。这些年,不管风浪如何大,研究所原有的植物分类、植物化学、植物生理等三个研究室和一个植物园,始终没有被冲掉或搞乱,而且还逐步地填补了一些空白领域。种下坚实的种子,就会长出茁壮的幼苗。仅仅几年的功夫,正是有些兄弟研究机构感到植物资源利用问题多、搞不开的时候,他们却感到海阔天空,有搞不完的题目。他们为冶金工业所急需的一种试剂染色素找到了大量的资源;他们研究了对治疗癌症有良好效果的美登木和它的近统植物;他们鉴定出了一种从埃塞俄比亚引种进来的优良的油料植物小葵子,并为之确定了引种地域和条件;他们搞出了多种激素,还引种了大量经济价值很高的植物。 但是,“庆父不死,鲁难末已”,“四人邦”不倒,国无宁日;一九七六年,到处都有一些“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怪物在闹!闹!闹!三月份,他参加了一次会议。看到那些帮派头目在大搞批斗为了签名、申讨,把人搞得懵头懵脑,他弄不清这是怎么一回事。但是他看得出来,在这里是什么事也干不成的,会还没完,他拔腿就走了。 这一趟他走得很远,一口气跑到了西藏,跑到了喜马拉雅山里。多年来,为了弄清中国的植物区系,寻找植物资源,他跑遍了全国各地,唯独西藏他没有去过。他是多么向往这块地方。有人说这里是不毛之地,但是在他看来,西藏是一块宝地。这里同云南一样,有热带、亚热带和高寒地带。河谷地带与西双版纳差不多,但纬度要高五到六度,是世界热带中最高最北的热带;森林面积比云南大得多,仅次于东北,而且针叶林树木的生长速度和单位面积的蓄积量,为世界之冠。畜牧基地非常广阔,不亚于新疆、青海、内蒙古。还有一点最重要,那就是西藏大高原占全国土地六分之一,绝大部分处于半开发状态,正是广阔天地大有可为,需要全国了解这里的条件和资源,为将来的进一步开发提供依据。这对我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事业有着极其重大的关系。 行前,上级领导,所里的同志,家里的亲人,老朋友,都来劝阻他。大家说年纪不饶人,不必去了,但他认为自己“虽然五十九岁了,但还没有到六十”。因为年纪不饶人,所以更要抓紧时间去。 这一趟,历时六个月,行程一万四千多公里,除了阿里和藏北地区,大半个西藏他都走遍了。在喜民拉雅山,他爬到了北坡五千四百米的高处。他对年青的科学工作者们说:“世界上的植物学家,眼睛都集中在这里。这是世界最古老的地方,也是世界最新的地方。你们在这里最少要认识六百种植物,这样,你们掌握的知识就活了!” 从林芝到墨脱,是一个沉积带。孟加拉湾的暖流在这里被高山挡住,年降雨量在二万公厘以上,每天倾盆大雨,好像整个太平洋的水都倾泻到了这里。这里的自然界是何等的宏伟、复杂和壮观。峰顶是千载玄冰和皑皑积雪,下来是流石坡、希疏的坐垫植物,再下来是草甸,再下来是丛丛暗针叶林,然后是常绿阔叶林,最下一带则是热带季雨林。他兴奋地对年青的科学工作者们说:“站在这里,好像有一个望远镜,再套一个放大镜,把整个世界的热带、亚热带、温带、寒带的植物,全都集中到你眼前来了!” 要离开西藏了,他连夜给昌都地委汇报。他要告诉在西藏工作的同志们,这里是祖国的一块宝地,是一个多好的地方!虽然它也有不足之处,但是缺点和不利条件,可以通过工作使之转化,而他的优点则是祖国其它地方所无法比拟的。我们要努力啊! 这次西藏之行,收获巨大。但是,他的健康却被损害了。由于高山缺氧,他满口的牙齿松动,有些脱落了。组织上送他到青岛休养,他在那里早六点起床,晚上十一点睡觉,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写出一本《西藏植物名录》。 英明领袖华主席和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邦,扫清了漫天的阴霾。吴征镒感到自己年轻多了。他对记者说:“我今年六十二岁了,争取活到八十岁,做完下面的工作;一、全国的植物志,是我参加主编和统管的,现在才出十几卷,计划出八十卷,到一九八五年出齐以此为我国植物学的发展打下基础。二、中国的植被,这是个总结性的工作。要把中国有多少原始林、多少沼泽、多少草原弄清楚,预计明年完成,国三十周年献礼,这项工作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如果我能活到八十岁,肯定还要修改。三、云南的植物志要完成,西藏植物区系的研究要完成。四、如果有条件想把《新华本草(即他在“牛棚里写的那本),《长江以南中草药名录》分类工作搞出来,为中国的新药学打个基础。这么多的工作,要完成当然有困难,但不是我一个人在搞,而且我们的自然条件这么好,钥匙在我们手中!”
1978年3月27日 光明日报 第二版 |
版权所有 Copyright © 2015-2019 云南吴征镒科学基金会,All Rights Reserved 【滇ICP备05000394号】
地址:中国云南省昆明市蓝黑路132号 邮政编码:650201
点击这里联系我们